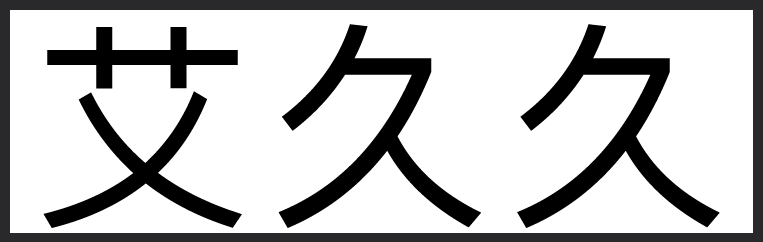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鼠疫》文摘 ——阿尔贝·加缪
- 北枫蔚然
- 2022-07-09 09:02:06
&2022年4月1日—6月1日 ⛳️SH
一部伟大的作品,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有些书本上的故事,倘若没有亲身经历,永远只是苍白无力的白纸黑字,难以共情。只有置身其中,故事才更加刻骨铭心。那两个月,终日闭门不得出,食不果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两个月吃了五十二包泡面的故事。一醒来就面对窗户大小的天空,真的不想醒来,偶尔写日记排解内心的绝望,也让自己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找到生命的安宁。
怎么办才能避免浪费时间呢?在时间的长河中体验。
靠正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又有可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问心无愧,这种前景足以令他心驰神往。如果说当初他接受了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那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的忠实不渝。
然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依旧执意写信,为了同外界联系,坚持不懈地设法,但是总要流于虚幻。我们想像出来的办法,即使有的得手了,也是一去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一连数周,我们只得重写一封信,重抄同样的呼唤,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从我们内心掏出来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无不丧失其内涵,变成空洞的词语了。就这样,我们机械地抄了又抄这些词语,试图用这些僵死的话语来传递我们艰难的生活信号。到头来,我们便觉得电文格式化的呼唤,要胜过这种执拗而枯燥乏味的独白,胜过这种同墙壁的毫无反应的对话。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结果他们势必强制自己,再也不去考虑他们终将解脱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来,可以说一直低垂着眼睛过日子了。不过,这样谨慎的态度,这种跟痛苦要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场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舍弃了十分常见的时机,不能躲进将来同家人团聚的欢乐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们就是这样,跌落在顶峰和深渊之间,上不上下不下,飘浮在那里,哪儿像活着,只是天天毫无方向地混日子,沉酒于枯燥三味的回忆,形同漂泊的幽灵,想要汲取点力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即使是流放,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流放在自家中。而叙述者体会到的,虽然只是全城居民的流放,他也不应该忘记像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他们则相反,离别的痛苦还要变本加厉,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受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市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因为他们固然同所有人一样,为拖延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牵挂着空间,他们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城中游荡的人,无疑正是他们:那是他们在默默呼唤唯独他们才熟悉的黄昏,以及他们家乡的清晨。于是,燕子的飞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的几抹光线,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这个总能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眼不看,固执地耽于他们那些过分逼真的幻景,竭尽全力追寻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种形态的光束、两三座山峦、钟爱的树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种种所构成的一种环境,在他们看来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如此一来,人人都得单独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这种普遍的消沉,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砺人的性格,但是眼下却开始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了。譬如说,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甘受晴天和兩天的支配。看那样子,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就让他们兴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有阴云密布了。几周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单纯地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反之,从这一列起,他们显然听任交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
从第二天起,塔鲁就投人工作,拉起第一支小队,随后其他许多小队也陆续组建起来。不过,叙述者谈到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无意夸大其词。我们的许多同胞,如今若是处于叙达者的位置,的确会经不起诱惑,难免夸饰这些组织的作用。但是叙述者宁愿相信,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领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这样一种看法,叙述者不能苟同。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人性中善的成分还是多于恶的成分,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在这里。人无知只有程度之分,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与恶行了。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矇昧的,而没有真知灼见明察秋毫,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那好吧,请今天晚上再过来吧。我派孩子去找他。”
二人离开时,朗贝尔问科塔尔做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啦。他们通过各个城门,将走私物品偷运进来,再高价卖出去。
“哦,”朗贝尔说道,“他们有同伙吧?”
“这还用说。
“站在战败者的一边。但是事后,我也思考了一下。”
“思考什么?”塔鲁问道。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能有壮举,但若不能有崇高的情感,我也不感兴趣。
〝我倒觉得,人无所不能。”塔鲁说道。
“不然,人就是不能长期忍受痛苦或者享受幸福。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人都无能为力。”
即使在城里,当局也想到将疫情格外严重的街区隔离开来,只准许执行必要公务的人员出人。一直生活在这些街区的人,都不免认为这项措施是故意捉弄他们。不管怎样,相比之下,他们就把其他街区的居民视为自由人了。而其他街区的居民身处艰难时刻,想象还有比他们更不自由的人,倒觉得有一些安慰了。“总有囚禁得比我们还要严的人。”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当时唯一可能心存的希望。
在挂着月亮的天穹下,城里排列着一面面灰自的墙壁、一条条笔直的街道,从未映现过黝黑的树影,从末被游荡者的脚步声或犬吠声打扰过清静。这座寂静的庞大城池,就完全化为死气沉沉的一堆高大的立方体,中间夹杂着一尊尊默默无言的雕像:唯独这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慈善家,或者永远禁锢在青铜躯壳里的古代伟人,还试图通过他们的石雕或铁铸的假面具,向人昭示世人曾经的光彩逐渐褪去的形象。在厚重的天幕下,在亳无生气的十宇街头,这些平庸的偶像高高居于宝座上,这些冷漠的凶煞,相当形象地展现了我们进入的僵死不变的统治,起码展现了这个世界的最后秩序,即由鼠疫、石头和黑夜组成的室息一切声音的大墓地。
不管怎样,正是这种明显的事实,或者这种直观的感受,维系我们同胞的流放感和离别感。在这方面,叙述者也完全清楚,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引人人胜的东西可以报道,该有多么遗憾,譬如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须知最不引人人胜的事情,莫过于一场灾难了,就是持续时间这一点,大灾大难就够单调的了。鼠疫流行的那些可怕的日子,在经历者的记忆中,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倒像无休无止的来回践踏,所经之处一切都被碾得粉碎。
最后,可以这样说,分离的人没有了起初他们赖以自保的这和特权。他们已经丧失了爱情的自私性以及从中获取的益处。至少是现在,形势已明朗:这场灾难殃及所有人。我们所有人,在城门口响起的叭叭枪声中,在印戳一下下敲出我们生死的节奏中,在一场场大火和一张张卡片中,在恐惧感和行政手续中,我们都注定死得颜面尽失,但是登记在册,在滚滚的浓烟和救护车悠缓的铃声中,我们都啃着流放犯的面包,都无意识地等待着同样忧心惨切的相聚和安宁。固然,我们的爱始终还在,但是派不上用场,成为负担,死沉死沉地附在我们身上,如同罪恶和刑法那样的不毛之地,完全化为一种毫无前景的耐性、一种执拗的等待。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有些同胞的态度,能让人联想到本城各处食品店门前所排的长队。同样安于现状,同样隐忍不言,既遥无尽头,又不抱幻想。这种感受还必须提升上千倍,才谈得上离别之苦,因为那是另一类饥渴,可以吞噬一切的饥渴。
在九月和十月之间,鼠疫牢牢控制着这座萎靡的城市。既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那么全城数十万人,还是一周又一周没完没了地原地踏步。雾气、炎热和雨水,相继统御着天空。南来的棕鸟和斑鸠,一群群悄无声息地飞越高空,绕开这座城市,仿佛惧怕帕纳卢神父所讲的连枷,这种安在房顶呼呼作响的古怪木质工具。十月初,骤雨阵阵袭来,荡涤了街道。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依旧是大规模地原地踏步。
然而,由于食品日益短缺,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引起忧感。我物活动猖獗起來,一般市场紧併的生话基本食品,有人以天价国。这样一来,穷苦人家生活就异常艰难,而富有家庭几乎什么也不嵌少。按说,鼠疫司职不偏不倚,卓有成效,本可以在我们同胞的心中强化平等,不料正相反,它通过自私心理的正常作用,在人心中加剧了不公正的感受。当然,最后还有无可挑剔的平等,即死亡,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争取。穷人饱受饥饿之苦,自然更加怀旧,想到毗邻的城镇乡村,那里生活很自由,面包也不贵。既然不给他们饱饭吃,他们就颇不理智地觉得,应该放他们离开。于是,一句口号终于流行起来,有时在墙上就能读到,还有几次在省长经过的路上有人喊出来:“不给面包,就给空气。”这句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号,也成为示威游行的信号:几次游行被迅速镇压下去,但是其严重性质则有目共睹。各家报纸接到指令自然服从,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读到这些报纸,那便是民众表现出来的“平静而镇定的动人典范”,标志着当前形势的特点。可是,在一座封闭的城市里,就亳无秘密可言了,谁也不会误解全城居民表现出来的“典范”。至于报纸上所谈的 “平静而镇定”,要想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需走进当局所组建的一处检疫隔离所,或者一个隔离营就好了。这时,叙述者恰巧被调往别处,不了解那些营所的情况。因此,他讲到这里,只能引述塔鲁的见证。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癌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癌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对,里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这一点您会清楚地看到),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以免稍不留神,就面对别人的脸呼吸,将疫病传给别人。天然生成的是细菌,其余的东西,诸如健康、正直和纯洁,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而人的意志永远也不应该停歇。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就是尽量少疏忽走神的人。真的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才始终不会疏忽大意。是的,里厄,当个鼠疫患者相当辛苦。不过不想成为鼠疫患者还要更辛苦。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很累,因为如今,所有人都难免染上点儿鼠疫。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有那么几个人,不想再当鼠疫 患者了,就尝尽了疲劳之苦,除非死了才可能解脱。
自不待言,鼠疫并未结束,这一点还有待证实。然而,在所有人的头脑里,火车已提前几星期发出,汽笛长呜,奔跑在一望无际的铁道上,轮船也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破浪前行。等到第二天,大家的头脑或许会冷静一会儿,再次产生疑虑。但是此时此刻,整座城市都晃动起来,离开那种封闭、阴暗而了无生气的方,即城建扎根,打下石基的地方,终于携带幸存者走了出来。那天夜晚,塔鲁和里厄离开林荫大道很久之后,走进僻静的小巷,沿着窗板紧闭的窗户漫步的时候,还听得到欢乐之声紧追不舍。由于疲惫不堪,他们也分辨不清是窗户里面悠长的痛苦呻吟,还是回荡在稍近的街道上的欢乐之声。临近解脱的这张面孔,欢笑和眼泪交织在一起。
科塔尔却笑不起来。他想要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想:这座城市闹完鼠疫,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又恢复1日观,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塔鲁认为,鼠疫会改变,又不会改变这座城市,而我们同胞的最强烈的愿望,当然现在是,今后也一如既往是,就仿佛周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什么也不会改变,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能忘掉一切,即使加上多大的意志力也是枉然,鼠疫总要留下痕迹,至少留在人心里。可是,这个矮小的年金收人者却直言不讳,他对人心不感头趣,人心甚至是他最不忧虑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行政机构本身会不会改组,譬如说,所有机构是否还像以前那样运行。塔鲁只得承认,对此他一无所知,不过依他之见,可以设想所有这些机构,在瘟疫期间受到冲击,重新启动起来会有些困难。还可以想见,各种新问题会大量出现,给原先的机构至少提出改组的必要性。
夜晚没有搏斗,只是一片寂静。在这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到一种令人室息的静谧,在这具已经穿好衣服的遗体上方漂浮,而这种静谧,在许多天之前的一个夜晚,在有人冲击城门之后,也曾出现在高踞鼠疫之上的屋顶平台的上空。就在那时候,里厄便已经联想到他眼睁睁看着死去的一些人在床上升起的这种寂静。到处都是同样的暂停,同样庄严的间歇,总是战斗之后的同样的平静,这便是失败的静默。然而,现在笼罩着他朋友的沉寂,显得密不透风,同街道和解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那么相得益彰,里厄由此清楚地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大夫不知道最终塔鲁是否找回安宁,但至少此时此刻,他自信已经了解,他本人永远也不可能安宁了,正如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赢局,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被剥夺了希望,仅仅带者自己的见识和记忆去生活,日子该有多么艰难啊。塔鲁恐怕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已经意识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该是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希望,就谈不上安宁,而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处死任何人,可又知道谁都可能情不自禁地判处别人死刑,甚至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刽子手。因此,塔鲁五内俱裂,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来就没有萌生过希望。莫非为此缘故,他才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而获取安宁吧?老实说,里厄无从知晓,这也并不重要。塔鲁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双手紧握方向盘为他开车的形象,或者这副厚重的身躯,现在躺着不动的形象。一种生活的热情和一副死亡的模样,这就是认识。
二月一个晴朗的拂晓,四面城门终于开放了,本市居民、各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省政府公报,无不欢呼庆贺。叙述者也就责无旁货,应当记下城门开放后的欢乐时刻,尽管像他这类人还身不由己,不能全心投人欢庆的行列。盛大的欢庆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与此同时,火车站里的列车开始启动,黑烟滚滚,不少轮船也朝我们的港口驶来,车船都以各自的方式表明,对所有饱受分离之苦的人来说,这一天是大团圆的日子。叙述至此,也不难想象,分别居住在我们多少同胞心中的离恨别痛,己到了何等苦不堪言的程度。白天,驶人本市的列车与开出的列车都同样满载着旅客,他们都早早预订了这一天的车票。在暂缓撤销禁令的两周期问,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到最后时刻,省政府又取消这一决定。在驶近本市的旅客中,有些人还末完全排除恐惧的心理,他们固然大体上了解亲人的命运,但是对其他人和这座城市本身,却不堪了了,不免把市容市貌想得面目狰狞可怕。不过也是仅仅对整个这一时期没有经受爱情煎熬的人而言,情况才确实如此。
他们当中一些人仍然孤孤单单,继续在城中游荡,再也见不到他们等待的人了。没有两次遭受离别之苦的人,总算是幸运者,而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在瘟疫之前,没有一下子建立起情爱甚笃的夫妻关系,又多年盲日追求十分勉强的结合,结果情不投意不合反成了冤家。这些人也跟里厄一样,轻率地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不料他们的分离送成永诀。不过,还有一些人,就亳不犹豫地找到了原先已经以为失去的人,譬如朗贝尔,这天早晨里厄跟他分手时还对他说:“鼓起勇气,现在这样才是对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感到幸福。现在他们知道了,这世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人总是渴望,有时也能获得的话,那就是人之间的温情。
但凡有人追求超越人的、连他们本人都想象不出来的什么东西,那就根本没有答案。塔鲁似乎重返他曾谈论的难得的安宁,然而,他仅仅在死亡中才找见了,到了这种时刻,安宁对他也毫无用处了。里厄看到在夕照中,站在门口紧紧搂抱在一起的人相互凝视,彼此传递着欲火。如果说这些人已经如愿以偿,那也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正是唯一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东西。里厄拐进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街道时,心里便想到,这些人只求平凡做人,满足于自己那种可怜而又可厌的爱,他们至少时而得到欢乐的酬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恢复的寂静中,时间一分一秒,似乎过得十分缓慢。忽然间,他们望见一条狗,从街道另一头窜了出来,那是很久以来里厄所见到的第一条脏兮兮的长毛猎犬,估计是主人把它掩藏至今,正沿着墙根儿小跑。跑到那栋楼的楼门附近,狗犹豫了一下,先是坐到地上,然后翻身倒下咬跳蚤。警察连吹几声哨子,召唤那条狗。狗抬起头,接着决定慢腾腾地横过马路,去嗅那顶帽子。与此同时,从三楼射出一发子弹。那条狗好似烙饼似的翻倒在地,四条腿乱蹬,最后仰身躺倒,抽搐了好半天。对面楼里当即还击,五六声枪响,对面那扇百叶窗被打飞好多碎片。继而,周围又寂静下来。太阳沉下去一点儿,阴影开始爬近科塔尔家的窗户。大夫身后的街上响起轻轻地刹车声。
清冷而辽阔的天空,在楼房上方闪烁,而靠近山峦那边,星星犹如燧石,显得异常坚硬。记得那天夜晚,他和塔鲁登上这座平台,将鼠疫抛到一边,而这天夜晚的情景,并没有多大差异,只是悬崖脚下的大海涛声更为喧响。空气轻盈,纹丝不动,释去了秋季暖风送来的咸味。然而,市区喧闹的声浪,还一直拍击着屋顶平台下面的墙脚。不过,这是解脱之夜,而不是反抗之夜了。远处那片暗红色的亮光,标志着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值此解放的夜晚,渴望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正是那种吼声一直传到里厄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