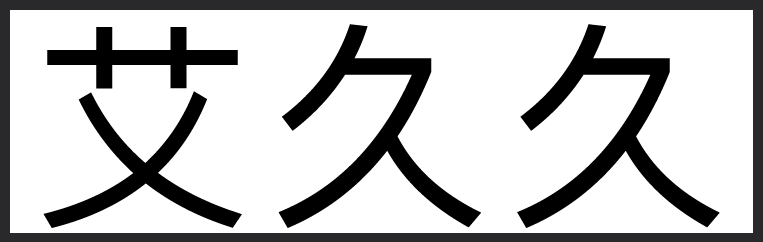断祭 三十三
- 不得说你说
- 2022-07-10 00:41:57
肖战进入片刻休整,缓过来后立马将人推开。
“离我远点。”
若是待会下手没轻没重,一具死尸不算难事,可眼下还不能逞一时之快,今日之事只能当作是被猪拱了。
王一博双腿不便,拖着半个不能动弹的身子,挪动十分缓慢艰难,看样子倒像是被糟蹋的那一个。
肖战见状拽住那只离他很近的白皙小腿,一路往脚踝滑去,而后猛地拉往自己腰间侧边,人落在自己怀里,“做出这副可怜样是要激怒谁?嗯?”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一床的东西凌乱,肖战胡乱拿起一根玉石,做势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好像将怀里的小美人吓到了,不仅一声不吭还有些害怕似的往他怀里躲。
肖战笑的很嚣张,“刚刚大国师可不是这样,怎么?这是又在演哪出呢?”
半晌没人应话。
“问你话呢,贴着我脖子做什么?”肖战被人搂着,看不见对方的脸,有些嫌弃的将人推开了些,却又立马被人粘上,“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松手。”
良久还是没人吭声,也不见人松手,肖战这才低头看了看,发现某人好像被吓哭了,小美人窝在自己怀里,眼角红红的。
。。。。
这人是妖怪变的吧?这里难道有外人?还演上了?
今日之事说出去,就算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瞧瞧这柔柔弱弱的样子,这小可怜见的模样,这般委屈的窝在他怀里。
造孽,绝对是造孽!!!
肖战丢了玉石,一脸不耐烦道:“你一个大男人这样也不怕人笑话!”
堂堂七尺男儿,哪儿能说落泪就落泪?
可是,也不知是谁刚刚哭的那么凶,一边舒服的要死,一边捏着人手肘说不许停,当真霸道的很。
玉石被丢,王一博立刻将人扑到,再不是刚刚软糯的样子,而是之前的模样,叼着对方的下唇又咬又啄,又欲又勾人。
。。。。。。
肖战是不想的,真的,他是这么想的,可这夜还长着,奈何对方又这么想,而且,看这人刚刚的样子,好像也不是很熟练,身子不便的人应该从来没有这样玩过,这是在这事上得了趣?身子不便又怕疼,这事好像确实轮不到他头上。
肖战忽然惊觉,他为什么要迁就他?为什么要让一头猪连着拱两次?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偏离,该不该越界的也都越了,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差,既然一次都做了,那两次跟一次又有何区别?
“你能不能装的久一点?你刚刚不是在哭?”肖战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任人趴在自己胸腹前乱摸,“再装装刚刚的小可怜样,别说,还真挺像那么回事。”
王一博拱着人脖颈啃了半天才停下。
“谢文宣养了外室。”
“外室?”肖战皱眉,“他一个上门女婿,还敢有这种念头?”
汤守成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选了一个读圣贤书的人做女婿,是因读书人老实本分,会待自己女儿体贴,虽说不是真正的上门女婿也差不多,就连当初成婚的府邸,也都是由汤府一手置办。
“那女子有了身孕。”
“有了身孕?”肖战只觉这些人做的事,一个两个都那么的可笑,明明打着软饭男好好夫君的招牌,府内无一姬妾却在外面养起了外室,“谢文宣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就不怕汤守成将他大卸八块拿来祭天?再说谢仁祖头上的两个哥哥都已陆续成家,这谢仁祖也到了婚娶的年纪,谢文宣这样做图什么?”
一个人总不会无缘无故断送自己的命。
“此女原是歌妓与谢文宣故去的表妹颇为神似。”说起正事,王一博躺在一旁不再乱动,“眼下这孩子能牵制谢文宣。”
“这么看来这位谢大人还是个念旧的人。”肖战说完挑起小美人的下巴,“你抓了他这个把柄,是想以此让他在你与上官倬之间周旋,做个两面人?你就不怕谢文宣把你给卖了,转头去给上官倬卖命?”
若是对方互通,这些伎俩实在是不堪一提,虽说这女子入不了谢府,可这孩子总有一日要认祖归宗,到时候能帮上忙的还得是大冢宰,区区一个国师的面子,汤守成又怎么会给?
王一博没有说话,而是凑上去亲人一口,肖战没有躲开,像看傻子似的看着对方,“说话就说话,你亲我做什么?”
王一博凑上重新亲,“见你想我如此。”
???
肖战被人压着,无奈道:“我何时说过?”
“你一直看我。”王一博像个要糖的小孩,一直词不达意却又勾人之甚,“谢文宣不会同上官倬说这些,因为汤守成还在。”
汤守成不会让那女子活命,更不会让一个孽种出生。
弃谁留谁,一眼可见。
“若谢文宣从未想过给这母子二人留活路呢?” 肖战冷笑将小美人反压过来,“你有没有想过此刻的谢文宣,也许正坐在上官倬府中喝着茶,商议着如何除掉你。”
王一博看着人笑。
“笑什么?不信?”肖战咬了王一博肩头一口,“疼不疼?”
王一博还是笑不说话。
“皇亲国戚就是好,知道上官倬不敢动你,就这样肆无忌惮的去拉拢他的幕僚,可我怎么看着,这压根不像是想跟谢文宣合谋的意思呢?你这是要他们窝里反,斗个你死我活啊。” 肖战忍不住跟着笑起来,“就是不知这里面的算计可有我呢?是不是想着一举把我也给弄死?”
“何以见得?”王一博望着人,“你死于我何益?”
“这谁知道呢?或许国师就是有这种掌弄人于无形之中的快感也说不准,毕竟你担这国师一位也不完全是凭空得来的不是吗?狗皇帝在位的这些年,未有过什么大的过错,但其行径荒诞至极,不仅当堂踹朝臣,还曾祭祀翻供台,这些也就罢了,可偏偏这狗皇帝还有好男风这个癖好,皇嗣不比寻常人家,若是宗亲过继,这可是会改江山的大事。”肖战低头望着王一博的双眼在笑,“所以,为何狗皇帝会同意钱氏女入宫?他可是连太后的懿旨都可以不遵的人,又怎么会一夜之间改了心意?我还听说,国师那一夜都在宫中,就是不知发生了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肖战下巴磕在王一博的锁骨上,“狗皇帝被人掌控不自知。”
王一博没有辩解。
肖战笑着继续道:“怎么不反驳?”
“在你眼中,我是这样的人?”
“不是…”肖战先是否认,而后凑近人耳畔,轻声道:“是远比这还可怕的人。”
看不见底的人。
肖战伸出舌尖触碰到对方的耳骨,“像你这样的人,谁都靠近不了,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太善良了,而你的心里埋着的是深渊,是黑色的幽静之地,你会把他们吓到,所以你会对他们隐藏,他们也都不懂你。”肖战舔着王一博的喉结,手已不知不觉搭在一物上轻拢慢捻,“但你的煞气会招引我,你的狡邪会呼唤我,知道为什么吗?”
王一博不说话,神情有些冰冷。
“因为我是你的同类,所以我知道你想杀我,就像我想杀你一样。”
能弄死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人的快感无可比拟。
“是吗?”王一博一把将人小手拽住不给再动,“那还要继续吗?”
两个宿敌在一起,这样看着好像不太对。
“看来国师是真的一点都不行。”肖战想着给人伺候的舒服,看人的双眼都有些迷离了,奈何对方竟丝毫没有反应,“有些事儿只能觉得可惜了。”
肖战阴阳怪气,王一博不再端着,按着人重新来一遍,比之前还要凶。半推半就的二人又上演了一番,将门外的人惊掉了下巴,连滚带爬的跑了。少年一路神神叨叨,一直说肖战会妖术,给他家主子下了咒,否则不可能会这样。
暖袖阁,君王将手里的奏折扔了。
已经连着几日有大臣上奏为肖战请官一事,按理来说一个他国之人不可能封什么官位,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上官倬的义子,这蛇鼠一窝的行径将君王激的火气不知何处发泄。
“陛下。”老太监尖细的嗓音响起,跪在暖阁外道:“王后求见。”
这个时候还能来人,不是勇士就是没眼力见。
“孤乏了。”君王并不想见什么人。
片刻,暖阁外没了声响,君王以为人已经走了,独自在暖阁内徘徊,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肖玄入冷宫已有些时日,这些日子祁恒毓身边不缺什么人,宫中的嫔妃不多,但男宠比比皆是。
“陛下。”王后还是进来了,唤了君王一声。
祁恒毓对他这个王后没有男女之情,因自小相识比得旁人要宽容些,毕竟还是王后,总不能因为一句话没有顺了他的意就罚了。
“王后这么晚前来是有什么事吗?”君王背对着人,连看都未看人一眼,“不日便是太皇太后的寿宴,听闻王后近日诸事操劳,有心了。”
体己的话也就是明面上的客套,君王在想的是怎么给肖战定罪。
“陛下不回头看臣妾一眼吗?”王后特意洗漱装扮前来,见君王如此待她,原本凉薄的心又觉冷了些,“可臣妾今夜要说的事,陛下或许会觉得有趣。”
有趣?
君王将手一抚于背后依旧未回头望人,“那就说来听听。”
“姑母赐的香有问题,国师的腿疾之所以一直未愈,也是与此香有关。”王后几步缓缓朝君王走去,从衣袖里拿出绢帕,“这是香料的配方,陛下不妨差人过目,这其中有两味不仅会使人无力,且会阻碍男子的能力。”
俗称肌髓散。
这种香毒性缓慢,若是经年累月的久闻,轻则让人双腿收缩,重则全身皆瘫,只剩意示尚存。
祁恒毓收了药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你想要什么?”
“陛下放心,臣妾今夜前来,并非逼着陛下与臣妾同寝,而是…”王后浅浅一笑,“臣妾想同陛下要一个人。”
“什么人?”
祁恒毓直觉眼前的王后已不是刚刚入宫的钱氏女,这样偷来太后的秘方,然后让他知道,这其中绝对有所求。
“臣妾要一个男宠。”
狗皇帝曾许诺王后,中宫可养男宠,且人数不限。
只是这些年从未听过王后有此需求。
“谁?”祁恒毓觉得事情不简单。
王后又笑,“臣妾不与陛下抢新宠,只是看中了冷宫里的一个人。”
果然。
祁恒毓冷了脸,“除了他,其他人任选。”
他亲自养过的一条狗,就是死也得死在他边上。
“陛下果真不信守承诺。”王后摇头而后自己寻了椅榻坐下,“只是陛下手里的帕子只有一半的配方,还有一半尚在臣妾手里,如何决断皆在陛下一念之间。”
敢威胁君王,祁恒毓冷笑一声,并未立刻做出抉择。
“陛下,臣妾活的时间不算长,可知道的一些事并不少,但陛下放心,臣妾与姑母不是一条心,与臣妾的父亲也不是一条心,臣妾永远站在自己夫君这边。陛下若是要臣妾死,臣妾一定会笑着去赴死,没有一句怨言,只是,这剩下的半个方子,陛下或许永远都拿不到了。”
一个女人若是真疯起来,比男人要可怕的多,尤其是一个心死的女人。
“那就带着方子永埋地下。”祁恒毓回过头望着王后,“孤不会送你走,而是你的姑母亲自送你去。”
王后或许猜到了这样的局面,只是她深信并非是冷宫里的人让君王如此淡漠,而是如今的君王不会再受任何人的胁迫,曾的幼崽已经成了一国之主,即便是再傀儡的皇帝,终究还是一个帝王。
“臣妾是不是惹得陛下生怒了?”王后说着似是而非的话,又继续往下道:“若陛下不愿臣妾将人带走,那不妨让人将其送出宫,不去别的地方,就待在国师府。”
“国师府?”
“不错。”王后反问:“陛下以为如何?”
君王尚在思铎,却听殿外一阵嚎叫,“陛下!不好了!冷宫出事了!!”
出事?
祁恒毓想都未想疾步出了殿,抓起小太监的衣襟,“他怎么样了?不是让人看着的吗?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小太监的帽子都歪了,吓得脚软,“奴才不知…只是禁卫大人冲进去时,已经见人双腿都是血了,也没人知道会这样,毕竟肖美人沐浴,从不让人在身旁伺候。”
君王将人甩到一旁,连轿撵都未让备,只身一人往冷宫跑。
“咱家踢死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大半夜的哀嚎什么,没见着王后和陛下在殿内议事吗?再说了,那不就是个冷宫里的东西,见点血怎么了?”老太监年纪大了,踢了一脚那不长眼的小太监一脚后赶忙跟上,“陛下!!!当心!!陛下!!!”
小太监委屈,明明是来通传的,却无缘无故被踹了一脚。
王后出来,未见失仪,“何事如此慌张?”
小太监扶了扶帽子,重新跪好回话,“回王后,冷宫里的肖美人好像自残了,等人赶到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且双腿都是血。”
“去请太医,不少于十人。”
“喏。”
王后随后也往冷宫去,身旁跟着一直随身的大宫女,而这位王后一路回想的是她今日白天与肖玄见面的场景,不得不说,跟冷宫里的这位相比,她疯的还不够彻底。
肖玄在冷宫过的还算惬意,除了将破败的庭院打扫干净,闲来无事还会看书作画,有时候还会抓几只鸟来玩,虽然他也不知道这大冷天的从哪儿来的鸟,又为何都往他的院子里飞。冷宫里的饭菜从来都是残羹冷炙,主子吃的不如宫人是常有之事,可偏偏他的饭菜与一般宫人的吃食无异,虽说没有大鱼大肉,倒也都是新鲜的。
直到这一日中宫王后来临。
肖玄见人前来没有过多的讶异,而是遣退了宫人在院子里守着,他和这位王后一同坐在凉亭喝茶。
“冷宫茶水不比中宫,王后娘娘见谅。”
王后没喝茶而是一直盯着肖玄看,她这样看他还是在几个月之前,那时的肖玄荣宠正盛,还尚未委身于这冷宫之中。
“想离开此处吗?”王后开口,“本宫可以让你出去。”
“王后今日是携了陛下的旨意前来?”肖玄浅笑道:“陛下让我待在哪儿,我便会一直待在哪儿,抗旨不遵的事不敢干。”
肖玄的言外之意,除了君王的话,他谁的话都不听。
“肖美人在陛下面前也直呼这个字?”
这个“我”在宫中是禁忌,这宫中无人敢随意用这个字,因为入了宫便是奴才,即便是身为中宫王后的她,也不可用这个字。
肖玄笑笑,“不知王后今日来此处是为了什么?我一个冷宫的戴罪之身之人,实在是想不明白,也不能意会王后的用意。”
“你很聪明,可这宫中不适合你。”王后说完将茶水浇到地上,“这杯茶本宫敬母后,想必母后也同意儿臣之举。”
母后?太后?
肖玄不明白王后为何好好的,突然要用这种祭奠已故之人的方式,敬茶给还在人世的太后。
“可是好奇?”王后放下茶盏,解了肖玄的疑惑,“这杯敬的是陛下的生母,愔榕王后,本宫与陛下的母后。”
帝后一体,后宫的人再多,也不可以称一声母后,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肖玄对狗皇帝没有感情,所以谁叫谁母后,谁又叫谁父皇,叫什么他都毫无触觉,即便是此刻狗皇帝蹦出一个儿子来,他也是这样纹丝不动。肖玄和肖战拿捏的领域不一样,一个擅长操控人,一个擅长蛊惑人心,虽然兄弟二人都有过人之姿,可肖玄天生男生女相,本就偏阴柔,加上骨架比肖战还要小些,看着就像是常年体弱的文弱男子。
“可知陛下为何好男风?”
肖玄饮茶不语。
“因母后让陛下喜欢谁,陛下就会喜欢谁。”
钱氏的一句话,仿佛一块巨石砸在肖玄面前。前王后让他喜欢谁,他就会喜欢谁,这是…何意?
“想必你也已看出,陛下心中有一个不可言说的人。”
“王后。”肖玄打断王后的话,“我眼下身处冷宫,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有些机密之事,王后还是别对我言尽,否则日后,我怕王后会后悔。”
“怎么?你还打算翻身?”王后笑笑,将巾帕放在石桌上,“有些话,可能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过,其实陛下一直以来发泄的,仅仅只是肉体而已,身处他身之下的可以是任何人,不仅仅只限于你一人,明白吗?”
曾经的每月春宫图,到如今的夜夜新人侍寝,君王从未变过,他从来不曾因哪一个人变过。
“既然王后将话说到这个分上,那容在下斗胆问一句,王后可是完璧之身?”肖玄这话问的有些不要命,几乎是踩在王后的逆鳞上,“既然陛下不曾变过,王后今日又为何来见我?”
这岂非有些此地无银?
王后不见动怒,未回答自己是不是完璧之身,而是倾笑后道:“是与不是都不妨碍本宫用这个同陛下换你入本宫的宫苑。”
“王后这是何意?”
“或许你会出宫。” 也不能说一定会入她的宫殿,但王后看上去似乎有十足的把握,“本宫今日来,只是想让你看看真实的陛下,不论你用什么法子,用任何手段,都抵不过他心中那个不可言说的人。”
“用这个?”肖玄指着巾帕上面的字道:“王后果然是中宫之主。”
这是下了血本,拿了什么机密来换他?
君王入院时发现庭院干净异常,再入殿看见肖玄昏迷躺在榻上,一旁守着的是那日的禁卫。狗皇帝原本急躁的心绪瞬间怒不可遏,未再靠近一步,而是冲着殿内跪地的宫人发火,“都死了是吗?太医呢?!!”
宫人跪地一片,瑟瑟发抖,“回…回陛下…已经去请了。”
“卑职看守不当,请陛下赐罪。”禁卫跪地。
“那就等他醒了,再赐了自尽。”君王将人草草定罪却端着始终不看肖玄一眼,“他怎么样了?死了还是活着?”
肖玄是疼晕的,此刻睡在榻上的眉头还是皱的。
“肖主子的双膝…”禁卫欲言又止。
此刻肖玄盖着被子,双腿如何狗皇帝看不见,王后与太医院的人同步而来,朝人行礼后便立马进去殿内救人。一群资历深的太医,入宫行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这番场景,被褥打开后,肖玄的双膝看的吓人,虽然已经被禁卫简单包扎止血过,可仍旧有些触目惊心。
血腥味伴着太医的叹息,肖玄不知是被吵醒的还是痛醒的,反正是醒来了,小脸无辜的看着好几张陌生的面孔,有些惊慌失措。
君王冷冷道:“都出去。”
“是…”
太医自觉退散,殿内只剩君王还有王后在,禁卫也黯然退下。肖玄没有如愿得到君王的怀抱,却反被勒住了脖梗。
“谁让你这么做的?”祁恒毓的手带着十足的劲儿,双眼望着肖玄,丝毫没有怜香惜玉,“谁让你动你的腿的?”
肖玄说不出话,看着一旁的王后。钱氏冷漠的像个木桩,岿然不动,冷眼旁观。
不得不说,这一招走的很险。
肖玄明知道狗皇帝心中藏着的人是谁,也知道这人的身子与旁人有所不同,可他还是敢这样去做,挑断自己双腿的筋脉,在老虎头上拔毛,太岁头上动土。
“孤问你话!!!”祁恒毓双眼通红,拧的对方的脸乌紫,就连自己的手也是青筋暴起,“为何要这么做!!!”
“陛下。”钱氏开口,“此人身份特殊。”
“出去!!”
君王让人离开,王后没有继续求情,也是,这情她刚刚已为人求过,至于下场如何,结局如何,那就看造化,看天意。
狗皇帝终是没有下死手,在人命悬一线之际松了手。
肖玄大口呼吸,此刻腿上的伤比不得刚刚的谋杀,心中多日积怨的气和腿上的伤一起给了君王,“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你在跟谁说话?”祁恒毓单手就将人下巴紧紧捏住,“谁教你的这招苦肉计?”
什么苦肉计,这叫放手一搏。
肖玄垂首不说话。
“怎么突然哑巴了?刚刚的气势去哪儿了?让孤走,好大的胆子!!!”
肖玄还是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手心紧紧拽着被角,直到祁恒毓的手背有水滴落,狗皇帝才有一丝丝心软的迹象,却朝人吼道:“哭?还知道疼!!你断双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会痛?!!”
“你这么凶做什么,就是疼才哭。”肖玄说话的声音很轻,跟之前他威胁君王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现在就像是个被人丢弃的家狗,狼狈的要死,“你别碰我。”
“万金之躯。”
祁恒毓二话不说,凑上去将人嘴巴堵上,“孤给你惯的!!反了天了!!”
肖玄想推开无耻之徒,发现根本就是徒劳。
“几日冷宫给待的,规矩越发没有,还学会了自残,好啊,不是想变成瘫子吗?孤成全你,明日就下旨,你们兄弟二人的腿,一个都别想留!!”
“此事跟兄长无关!!”肖玄咬了狗皇帝一口,疼的又掉了几滴泪,挂在脸上显得特别好看,“你这个昏君!!”
昏君都出来了,君王不知怎得笑出了声。
祁恒毓心里其实很复杂,他并没有多爱肖玄,也知道自己对他仅仅是肉体的迷恋,可不知为何,眼前这个小蛮子就是能这样轻易将他激怒,让他心口一坠一坠的不安。
“不想你哥出事就老实点!!”君王威胁道:“你的腿能保成什么样,他的腿才能怎么样。”
肖玄哭的很凶,抬手抹眼泪,“你就知道欺负人,从来不会听我说什么,都是一味按照你的性子来,还这么霸道专制,兄长有什么错?如果他有错,那上官倬为何要收他做义子。”
原来在这等着。
“怎么?想要孤赐死上官倬?”祁恒毓邪魅一笑,“什么时候,你这小脑子里的算计,能不要这么让人一眼就识破?”
肖玄撒娇不会硬撒,得有人懂,比如狗皇帝这个时候就知道给人顺话,“疼的都冒冷汗了吧,这可怎么办呢?”
“知道我疼还把太医赶出去?”肖玄趴在君王肩头撒娇,眼泪跟下雨一眼往下淌,“疼,好疼…疼的都要死了…”
“胡说八道。”君王斥责肖玄,朝殿外道:“还不快滚进来!!”
太医匆匆赶进去救人,老太监不禁摇头,踹了门外的小太监一脚。
这是搞了多少假血,上演这么一出?
离宫一时半会是离不了了,至少在肖玄的腿彻底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