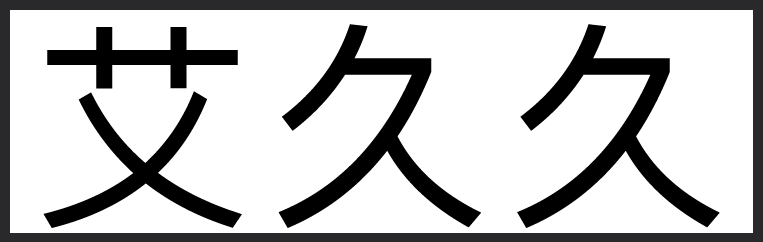今夜不设防6
- 阿泗阿泗_
- 2022-07-14 04:32:20
温克礼笑了一声,杨律洲抬起头来看他,温克礼说他长得好看,在杨律洲看来温克礼更好看,是一种更加让人亲近的长相,在他看来,是天生就适合做医生,救死扶伤的那类人。
他那张脸上总是时不时挂着淡淡的笑意,看上去温和,待人又谦和。在他拿烟的时候,才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漠然的漫不经心,让人更加挪不开眼。
温克礼穿着就是杨律洲的那双灰色拖鞋,温克礼在房间翻了翻才发现还有一双塑料拖鞋,也是灰色的,左脚那一只鞋中间脚掌的那一部分断了一半,能穿,但是难穿。他身上穿着的是杨律洲随手扔在沙发上的一件黑色毛衣,跟他那件圆领的有些像,穿上去更加宽松。
他一出来就打了个寒颤,然后杨律洲就把那双拖鞋放到了温克礼的面前,温克礼没换。站在蹲着的杨律洲旁边低着头问他:“杨律洲,你多少岁了?”
这是温克礼第一次叫他名字,杨律洲看了过去:“32。”
“嗯。”温克礼外面还穿着那件十分单薄的白大褂,双手插在兜里,“我27。”他捻了捻杨律洲抽完烟后残留下来的烟灰,总之那双白色的拖鞋他不换,也没问为什么说不抽烟的杨律洲今天抽了烟。
杨律洲递给他的打火机,他也没接。
杨律洲拿不准温克礼的想法了,坐在地上有些局促,准备起身的时候温克礼又说话了:“你对那个女人有意思么?”
杨律洲恍惚了两秒才反应过来,是刚刚那个女人。
“没有。”
杨律洲又回想起昨夜在鼓楼的那一场充满情欲的默剧,喉间紧了紧,闷着声终于起了身,还不忘将打火机烟盒还有拖鞋一齐装进黑色的塑料袋里,牵着温克礼的袖子进了屋。
“我给你留了早餐,你先把早餐吃了,今天有雪,外面冷。”杨律洲的声音依旧沉稳。
“然后呢?”温克礼望着杨律洲进厨房的身影,冷冷问道。
杨律洲静默了几秒,温克礼就等着,然后他听见杨律洲说:“然后我送你回家。”
温克礼淡淡地笑了一声,问道:“这就是你在门口抽了半包烟想出来的解决方式是吗?”
杨律洲端着一碗温粥,手小幅度地颤抖着,他低着头声音不太大。
二人沉默很久,但杨律洲还是回答了他。
但温克礼听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合适。”
温克礼临紧紧盯着杨律洲,这个相处了一个多月的男人,站在他家徒四壁的家里,手里端着一碗白粥,另一只手端着一碟从早市上买来的爽口的凉菜。
温克礼看笑了,他懒得去逼杨律洲去承认什么了,确认关系无非是让上床更理直气壮,虽然他们昨晚并没有发生关系。
他不知道杨律洲怎么想的,温克礼索性也不去想了。
他走到了杨律洲面前,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自然地接过了他手里的白粥与凉菜。
不得不说味道很好,至少比医院好。温克礼一向食欲不振,这次都却半口不剩,碟子里只剩着星星点点的凉菜的红油。
然后他换了鞋,对着收拾碗筷的杨律洲挥了挥手,“我走了,不用送,”
六个字说完就推开了门,杨律洲顿在原地,抿了抿唇,等他回过头看向窗外的时候温克礼已经出了院子门。
白色的大褂因风扬起衣角。
又过了几秒钟,引擎声响了起来。
大周末的早上的人也挺多,前面一个红绿灯,大十字路口,红灯还有六十秒。车水马龙也的确是车水马龙,温克礼情绪起伏倒是不太大,就是那碗粥吃得现在还有点堵,堵得心里难受。旁边一辆切诺基跟他的车开的挺近,但是大冬天的敞着车窗,温克礼隔了一扇窗都能听见张宇在CD里声嘶力竭地唱“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种貌合神离的心伤。”
温克礼觉得听着有点讽刺,他确实不难过,只是有些惋惜,杨律洲的身材很好,至少他见过的人里面比杨律洲好的没有。
算了。
温克礼收回了思绪,红灯已经跳成了绿灯。
他一路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思考,是不是自己的感情生活过于匮乏而让自己有了一个稍微亲近的人就有点儿什么想法,他数着一路上过了几个交警岗,顺便把跟杨律洲这个事捋了捋。
但你就是没办法,你得承认有些人你一旦接触了你就没法说想要分开,那种吸引力是很让人上瘾与无奈的。两个人到最后也没说开诚布公把这个事好好商讨商讨,只是模棱两可的两个人就盖了个章。
这个章就是“不合适。”
得,温克礼揉了揉眉心,再一露脸又是那位温和克礼的温医生了。
杨律洲在家把碗筷都给收拾了,那双扔在沙发上的乳白色的毛绒拖鞋他看了两眼,无奈地将它收到了柜子里。温克礼走得快,昨天换下来的衣服也都放在沙发上,杨律洲接了点热水在卫生间都给洗了,然后晾了起来。
以前杨律洲父亲还在的时候,就经常教导他,说,做我们这一行的,你不能碰那些有瘾的东西,一旦有了瘾,你连这些东西都承受不来,那毒品呢?几克毒品就能要了命。
父亲总是这么说,说的时候还抽着烟。杨律洲只觉得听着好玩,烟也是有瘾的,但父亲却抽,只是酒从来都不多喝。他原来对于父亲的说法不置可否,后来父亲一去不复返,于是杨律洲也开始效仿着记忆中的父亲学会了抽烟,承袭父亲警号事业去了云南,再然后他又回了北京。
有些东西有瘾,比烟更有瘾。
他在心里泛起苦笑。
越入冬,北京这天就越冷,西伯利亚寒流彻彻底底发了威,一月中旬了北京整个车流量人流量只多不少。游客占了得有40%,大多都是去一宫两园的。
温克礼这一个月就是连轴转,没办法,评论两天一台手术,他都忍不住想去后海那边看看有多少傻帽滑冰溜雪摔骨折的。
除了累就是平静,和往常一样平静。
唯一的波澜是张医生,温克礼的师兄回来了。
张师兄问杨律洲的事儿的时候,温克礼正在补病志,戴着一副无框的银细边眼镜。原本都该在忙碌中忘了这么个人的,忽然间被提起来温克礼有种游园惊梦的不真实感,他推开眼镜揉了揉眼睛,对着张师兄莞尔一笑:“杨警官很配合,十二月中旬就拆了石膏,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说完温克礼就低下了头,搓了搓手。明明办公室里的暖气足够热了,自己却还是觉得有点冷,可能是穿的毛衣有点松散,容易透风。衣服洗过很多次了,但温克礼低下头还是觉得自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松木香,让人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