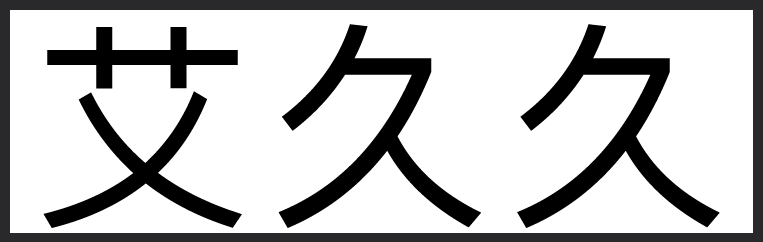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冰淇淋桶Ⅱ软糖记》第四十五章:神秘女子之来历
- 写文的尼罗
- 2022-08-04 04:32:53
傅西凉回到办公室里坐下来,身上汗涔涔的。把邮差包放在腿上打开,他拿出那包什么酥看了看,心想明天也用不着带这个了,就算在饭桌上不能敞开了吃,那么加上饭后那一大杯咖啡,也足够了。
他又想原来大帅府里的厨子也不过尔尔,手艺真不见得比二霞高明,而二霞一定比这里的厨子更年轻貌美。据他所知,一般的厨子都是油渍麻花的大汉,反正他家原来的大师傅就是那样。
想到这里,他很满意,因为自家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那么的整齐美观,让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很舒服。
这时,房门一开,正是送票子的人来了。送票子的人笑得慈眉善目,看着也很令他愉快。
*
*
这一天,就这么愉快的过去了。
翌日清晨,他斜挎着邮差包,很轻松的出了门,水壶和点心一样都没带。到了中午时分,他被一名勤务兵领去了老五老六的院子里。他算是叶烈真的客人,席上有客人的时候,老五老六就失去了上桌的资格,只能站在一旁伺候着。
饭后喝过咖啡,傅西凉照例独自往回走,结果走到半路,路旁又钻出了那位貌似姨太太的陌生女子。陌生女子挡在道路中央,冲着他开篇就是一声冷笑:“既然是根本已经不认得我是谁,那你昨天跑什么?”
傅西凉见了此人,先抬腕看了看手表——还好,今天早些,刚刚一点钟。
“我不是跑,我是急着去上班。”他答:“你找我有事?”
女子又是一声冷笑:“若说事,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和你见一面,让你看一看如今的我。”
傅西凉听她讲话难懂,而且从鼻孔里一声接一声的往外哼着笑,分明也不是个好笑。对于这种阴阳怪气来者不善的货,他的对策便是把脸一冷,拔腿就走:“不看。”
女子后退一步,抬手一挡:“不,不看不行,我今天就是要你看,要你把我看清楚!”
傅西凉见她先动了手,只得停了下来:“你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看!”
女子的一只纤纤素手停在了半路,停了几秒钟才缓缓放下来,叹息似的,她发出了苍凉的轻声:“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傅西凉被她缠了个莫名其妙:“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姓傅,我叫傅西凉,你找的是我吗?”
“我是这个月才知道了你名叫傅西凉,在此之前,我对你一无所知,就只知道世上有你这么个人。”
傅西凉扭头盯着路边一丛秋菊,思索了片刻,末了感觉面前这人已经是不可救药:“从昨天到现在,你一句明白的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找我干什么。我都说我不认识你了,你还对我纠缠不休,你到底想怎么样?”
说到这里,他扫视了周围路线,打算从路旁草地上兜个圈子冲过去。燕云说过,男女有别,年轻单身汉和别人家的姨太太更有别,况且就算她不是叶烈真的姨太太,他也不想和她多说。
他觉得她一点也不可爱——都不用她发冷笑或者说怪话,她单是细条条的往那儿一站,看着就已经是不可爱。
而那女子看出了他是作势欲逃,心中一时间五味杂陈:“你别走,听我说。你……你是救过我的命的呀。”
傅西凉听她越说越玄,忍不住问道:“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女子听了,百感交集,哭笑不得:“你还说我?看你这些天在大帅府里的所作所为,脑子有问题的明明是你。”
傅西凉听了这话,正要恼羞成怒,不料那女子又开了口,这回竟是把话说得十分明白顺畅,听得他也愣了。
*
*
傅西凉没有看错,这女子正是叶烈真的七姨太太,他昨天中午还在心里给人家起过外号,说人家是黄蜂老七。
黄蜂老七的出身,和二霞有些相似,也曾有过一个殷实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足够让她活得衣食无忧,长到了七八岁,家中也有闲钱和闲心去供她读几年书、认些许字。
她父亲爱玩,玩得不大回家,但只要是回了家,对她就总是笑呵呵,和她的母亲一样温柔可亲。她还有一个哥哥,哥哥也是个好少年。
如此风平浪静的活到了十八岁,忽然有一天,天上降下了个霹雳:她父亲欠了一屁股赌债,跳河了。
她父亲是爱赌,也不只是赌,好玩的他全爱玩,但全家一直以为他只是小赌,等债主子堵了大门时,她母亲打开保险箱子,才发现那里头的存折股票、契约文书全没了。她父亲不知何时成了家贼,把这个家蛀成了个空壳子。
她,她母亲,她哥哥,糊里糊涂的就成了穷光蛋,手中能卖的全卖了,全卖了也还是堵不上那个债窟窿。债主子放出话来,说是父债子偿,再不拿钱出来,就要拿她哥哥开刀。哪怕是把她哥哥抓去宰了听个叫唤呢,也绝不让她家就这么把账赖过去。
这话是恐吓,但即便不要性命,总被债主子这么日夜威胁着,也依然不是长法,所以她母亲当机立断,决定弃女保儿,把她卖了还钱。
然而问题又来了:怎么卖?
她们一家素日关门过日子,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不甚关心,如今让老太太去将一个大活姑娘卖掉,老太太想卖都不知道从何卖起。那时候她们已经无房栖身,三人挤在一家破客栈里。客栈倒是有人牙子,然而破客栈里的破人牙子们,门路有限,做不出什么体面的买卖来,逮着女的就是往窑子里卖,而且还全是下等窑子。
老太太感觉这不行,这么卖对女儿的人生太不负责。身为一位有责任心的老娘,她认为女儿最好是被一户有钱人家买去做丫头,再过两年被老爷收房做小才是最好,若有本事养出一儿半女,就更妥了,如果能够直接被老爷买去做小也行,只是女儿才十八,若遇上了个年逾花甲的老爷,那就还是不甚合适。要是四十来岁的话,倒也罢了。
老太太想到这里,一时无法,索性亲自带了女儿上了街去,也不敢往大街上走,畏畏缩缩的在条小街旁坐了,坐下之后往女儿脖子上挂了块纸牌子,纸牌子上面是她哥哥写的毛笔字,大概就是卖身救母之类的那一套话。
这条小街十分僻静,半天经过一个人,让老太太部分的保全了颜面,没有在众人的围观之下羞愤欲死,但颜面虽保全了,女儿却无主顾,若是这么一天接一天的拖下去,那帮债主子将儿子绑走了可如何是好?
老太太心潮起伏,且不必说,再说这个待售的本人——她当时已经是彻底懵了。
得知父亲的死讯时,她已是受了刺激;被债主子追杀着住进了那间破客栈,这又是一个刺激。及至昨晚看见她母亲和她哥哥坐在灯下,商量着如何卖妹妹才既能来钱、又有体面,她木呆呆的,只感觉看不明白:娘不是原来那个慈祥的娘了,哥也不是原来那个友爱的哥了。
她还听见他们最后达成了共识:最好是能把她卖进一户好人家里去,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不找这客栈里的人牙子。毕竟——她娘含泪吟道:“这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哇!”
她哥望着豆大的灯焰,也是流泪长叹。
经过了夜里这一场,翌日白天她坐在街边时,就非常希望能来个人把自己买走。她不想再回客栈里去了,和两个一门心思要把她卖掉的亲人住在一起,她只感觉寒气凛凛,整个世界都变得十分恐怖。
如此等到傍晚时分,傅西凉来了。
她那时当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就只见路口那边走来了一名大个子青年。青年做摩登的西装打扮,走路时有种特别的腔调,目不斜视,缓缓而行,及至走得近了,她看清楚了他的脸,发现他那种冷峻的相貌,和他那一路的步伐还颇相配,有点目空一切的高傲姿态。
青年经过了她们母女,随即停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钞票扔给了她们。她刚想辩解自己不是乞丐,然而他已经头也不回的走远了。
这张钞票救了她们,她们从昨天起就已经穷得断顿了。
第二天,也是傍晚时分,她在街边又等到了他。他还是那样走过来,丢给她们一点小钱,随后继续前行。
第三天傍晚,来的还是他。他那施舍的姿态很奇异,不带任何感情,甚至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们,但是一定要施舍,仿佛是奉命而来一般。
第四天傍晚,她忍不住了,在他经过之时,她小声的说:“先生,先生,你要丫头不要?你买了我吧?”
这回他终于看了她一眼,但她感觉他其实是并没有听到自己所说的话,他的眼中一片空荡。于是她也不要脸了,追着又道:“先生,先生,你要丫头不要……”
没等她把话说完,他转身又走了,仿佛她的话只是一阵风。
第五天,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有了他的施舍,她们这五天没有饿死,但她娘在这五天里又想开了一些,不会因为羞愧而一直带着她躲在这条小街上。也许明天她们就要换地方了,换了地方的话,就再也遇不到那位先生了。
于是,在这一天的傍晚,在如期的等来了那位先生之后,她没有去接他扔下来的那张零票子,而是忽然跪起来膝行到了他的跟前,说道:“先生,您要丫头不要?我原本也是好人家的闺女,因为家里欠了巨债,没法子,才要让我卖身还债。您要是肯买了我,既是救了我全家,也是救了我,我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伺候您。”
他低头看着她,眼镜镜片映了一片霞光,霞光之后是他疑惑的眼睛,他说:“不要。”
她急了,伸手去抓他的裤管:“求您了,我很便宜的,我什么都能做,我还念过书,我能写能算……”
她的双手先前撑在地上,蹭了满手的尘土,如今要去抓他的裤子,他便猛的向后一退。她先前对着他长篇大论,带着哭腔,声音刺耳,已经让他感觉不适,如今又要用脏手来抓他的裤子,让他越发感觉烦躁。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只依稀听见她让他“要她”,还说“她很便宜”。真是岂有此理,他只是想回家去,她为什么要对他纠缠不休?
眼看她要来抱自己的大腿了,他当即又退一步,大声说道:“不要!白给也不要!”
然后他转身便走。
她的精神本来也是濒临崩溃了,他是她在绝境中唯一的一点希望之火。她对他朝思暮想了五天整,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嫌弃着自己,他对自己竟然是“白给都不要”。
她像是被人抽了骨头,一下子就灰了心。如此又辗转了些天后,她终究还是被破客栈里的破人牙子领走了,临走的时候,她对母亲和哥哥只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好好过吧。”
破人牙子并没有把她送进下等窑子里去,而是把她转了手。她被个姓聂的官儿买了去。那姓聂的官儿有处秘密的外宅,把她放在外宅里养了好几个月,养得她细皮嫩肉,学了许多规矩,这期间,姓聂的又弄回来了一个十七的姑娘。把她和那姑娘一模一样的装扮修饰了,姓聂的拿她们当了一对礼物,送给叶烈真做了老七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