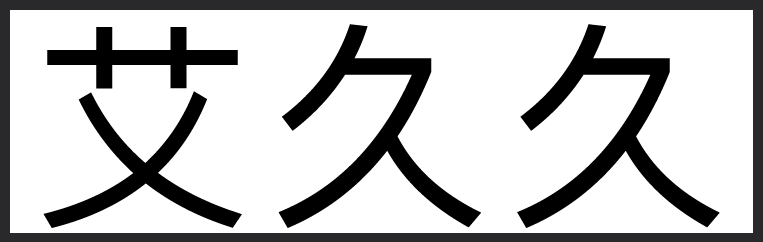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碟猪头肉与半生痴缠
- 以图说史
- 2025-05-18 19:00:00
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碟猪头肉与半生痴缠!
槟城的夏天湿热,芭蕉叶子耷拉着,陈璧君攥着油墨未干的《民报》,盯着“精卫”二字发怔。报上说,这人要“衔石填海”,把腐朽的清廷掀个底朝天。十五岁的她,啃着榴莲,指尖黏答答的,心里却烧起一团火:“这汪精卫,莫不是个神仙?”
父亲陈耕基的会客厅里,汪精卫一身月白长衫,眉眼清俊如画。他讲革命,声音像竹叶上滚落的露珠,脆生生又亮堂堂。陈璧君躲在屏风后偷看,手里的冰镇椰汁忘了喝,流淌出来,滴滴答答湿了绣花鞋。
“革命不成,何以家为?”汪精卫躲着陈璧君,像躲一碗烫嘴的肉骨茶。可这南洋姑娘偏不信邪——她退婚约、撕护照,揣着金条追到东京,给同盟会捐钱时一掷千金,活脱脱像菜市场买榴莲:“喏,拿去!不够再找我爹要!”
汪精卫写文章,她研墨;他演讲,她带头鼓掌;他蹙眉叹气,她立刻拍桌子:“四哥!缺钱还是缺人?”同盟会的老先生们打趣:“这胖丫头,倒像块粘糕,甩都甩不脱。”
北京胡同的冬夜,北风卷着煤灰往人脖子里钻。汪精卫裹着旧棉袍,对着炸弹图纸发愁。陈璧君突然推门进来,鬓角别着朵颤巍巍的绒花:“四哥,我陪你杀载沣。”他摆手:“这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也要一起掉!”她掏出英国护照,三两下撕成雪花,“这下你可信了?”!
临行前夜,她端来一壶烧刀子,脸红得像院里的红梅:“我没什么值钱物,唯有这副身子。”窗外老鸹哑着嗓子叫,汪精卫望着她粗布衣裳下笨拙的柔情,忽然想起槟城雨后的野栀子——不精致,却香得不管不顾。
菜市口的牢房阴湿,汪精卫嚼着发馊的黄米饭,忽见狱卒塞来十个鸡蛋。蛋壳上歪歪扭扭刻着“璧”字,附张字条:“忍死须臾。”他一口咬开,蛋黄流金似的淌出来,混着铁锈味的血丝咽下,竟比槟城的娘惹糕还甜。
后来他写《金缕曲》:“一腔血,为君剖。”陈璧君捧着信又哭又笑,把南洋带来的金镯子全熔了,换成银元疏通狱卒。辛亥年的爆竹声里,出狱的汪精卫叹口气:“罢,娶了吧。”
婚礼上,她穿大红嫁衣,笑得像颗熟透的山竹。
再后来,他成了万人唾骂的汉奸,她梗着脖子对法官嚷:“我丈夫是卫道士!”牢饭吃了十四年,临终前还念叨:“我家四哥,生得顶俊……”
汪曾祺写栀子花:“去他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陈璧君若读过,定要拍大腿叫好。这世间的痴缠,原不分美丑对错,不过是榴莲配普洱,烈酒就卤煮——滋味如何,终究是局中人才晓得。历史人物
槟城的夏天湿热,芭蕉叶子耷拉着,陈璧君攥着油墨未干的《民报》,盯着“精卫”二字发怔。报上说,这人要“衔石填海”,把腐朽的清廷掀个底朝天。十五岁的她,啃着榴莲,指尖黏答答的,心里却烧起一团火:“这汪精卫,莫不是个神仙?”
父亲陈耕基的会客厅里,汪精卫一身月白长衫,眉眼清俊如画。他讲革命,声音像竹叶上滚落的露珠,脆生生又亮堂堂。陈璧君躲在屏风后偷看,手里的冰镇椰汁忘了喝,流淌出来,滴滴答答湿了绣花鞋。
“革命不成,何以家为?”汪精卫躲着陈璧君,像躲一碗烫嘴的肉骨茶。可这南洋姑娘偏不信邪——她退婚约、撕护照,揣着金条追到东京,给同盟会捐钱时一掷千金,活脱脱像菜市场买榴莲:“喏,拿去!不够再找我爹要!”
汪精卫写文章,她研墨;他演讲,她带头鼓掌;他蹙眉叹气,她立刻拍桌子:“四哥!缺钱还是缺人?”同盟会的老先生们打趣:“这胖丫头,倒像块粘糕,甩都甩不脱。”
北京胡同的冬夜,北风卷着煤灰往人脖子里钻。汪精卫裹着旧棉袍,对着炸弹图纸发愁。陈璧君突然推门进来,鬓角别着朵颤巍巍的绒花:“四哥,我陪你杀载沣。”他摆手:“这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也要一起掉!”她掏出英国护照,三两下撕成雪花,“这下你可信了?”!
临行前夜,她端来一壶烧刀子,脸红得像院里的红梅:“我没什么值钱物,唯有这副身子。”窗外老鸹哑着嗓子叫,汪精卫望着她粗布衣裳下笨拙的柔情,忽然想起槟城雨后的野栀子——不精致,却香得不管不顾。
菜市口的牢房阴湿,汪精卫嚼着发馊的黄米饭,忽见狱卒塞来十个鸡蛋。蛋壳上歪歪扭扭刻着“璧”字,附张字条:“忍死须臾。”他一口咬开,蛋黄流金似的淌出来,混着铁锈味的血丝咽下,竟比槟城的娘惹糕还甜。
后来他写《金缕曲》:“一腔血,为君剖。”陈璧君捧着信又哭又笑,把南洋带来的金镯子全熔了,换成银元疏通狱卒。辛亥年的爆竹声里,出狱的汪精卫叹口气:“罢,娶了吧。”
婚礼上,她穿大红嫁衣,笑得像颗熟透的山竹。
再后来,他成了万人唾骂的汉奸,她梗着脖子对法官嚷:“我丈夫是卫道士!”牢饭吃了十四年,临终前还念叨:“我家四哥,生得顶俊……”
汪曾祺写栀子花:“去他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陈璧君若读过,定要拍大腿叫好。这世间的痴缠,原不分美丑对错,不过是榴莲配普洱,烈酒就卤煮——滋味如何,终究是局中人才晓得。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