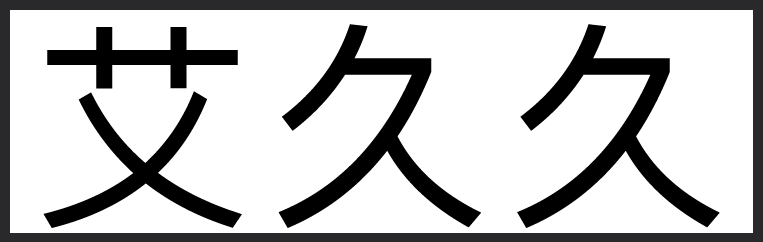昨晚进塔克拉玛干沙漠露营...
- 烧椒盖饭
- 2024-10-07 15:27:03
昨晚进塔克拉玛干沙漠露营,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沙漠里很冷,云层非常厚,完全看不到星空。
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再坐骆驼车,再徒步。天已经很黑了,徒步是止语的,营地的主理人大哥讲,不要说话,不要开手电筒,就用你的眼睛耳朵感受这里,看不到路就用脚感受沙丘的起伏。你的眼睛会适应的,会看到远处的沙丘的。
塔克拉玛干的沙子非常绵,我们大字形地躺平,大哥指着什么都没有的天空讲,如果是晴天,这里会是什么星,那里会是什么星,银河会是什么样的走向,他所指的地方,仍旧一片虚无。
然后非常意想不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音乐,很多种乐器,驼铃羊铃牛铃,充满沧桑的歌声,多个声部起起伏伏,夹杂着风沙的声音,好像千年以前的商队,人、马、骆驼,在丝绸之路的黄沙中行走。
那一刻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感动,那种感觉太当下了,我眼泪一下就掉下来。其实没有看到满天繁星,是有点遗憾的,但那一刻忽然感觉,能不能看到星星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星星其实就在我们头顶上,不管能不能看到,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
后来大哥点亮了火把,带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走上沙丘,看到演奏者和演唱者们,十几位当地的大叔和爷爷。后来才得知,刚刚的演奏离我们150米远,整个沙漠就是他们演出的声场,他们的嗓音、奏乐,都与沙漠融合地如此完美。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觉的民族音乐,体验感最佳的实景演出。惊喜是,我们进沙漠徒步的时候,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场演出。这些老者都是沙漠边缘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大多数都没怎么离开过塔克拉玛干,他们演奏的乐曲是维族最有名的古典音乐形式十二木卡姆,是非遗。
营地的主理人大哥一个一个介绍他们,介绍他们的乐器,请他们各自solo,有几个还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最年长的一位已经84岁了,他说听说今天有远方的客人,一定要跟着进沙漠演奏。还有一位74岁的老人,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300公里外的县城,只去过一次。他的solo没有起伏,放在我们的音乐审美中,他的技术平平。虽然那把木卡姆已经陪他演奏了五十年,但他其实只会那么两首曲子,一辈子翻来覆去也只是演奏那两首。
营地的大哥告诉我们,那首歌的意思是“当冰川的水融化,当小花帽挂在桃树上,我多么希望你回来,我死去的孩子”,我好像一下就明白了,这首歌为什么唱了五十年,还是这样平平。他的孩子不会回来了,他唱的就是他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南疆的人文,不在历史博物馆,在村落,在人。
我发现有几位演奏者就是我们进沙漠时,帮我们赶骆驼车的大叔,还有几个是帮我们烤羊肉串的大叔,整个营地,其实就只有他们这些人。
后来我们就在篝火边开始像少数民族一样疯狂跳舞了,然后反复跟身边的人拥抱。火焰在沙漠之中异常明亮,就像某种涌动不止的情怀。整晚手机都没有信号,一丝都没有,但是完全没有人感到焦虑,没有人不在享受当下那一刻。
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再坐骆驼车,再徒步。天已经很黑了,徒步是止语的,营地的主理人大哥讲,不要说话,不要开手电筒,就用你的眼睛耳朵感受这里,看不到路就用脚感受沙丘的起伏。你的眼睛会适应的,会看到远处的沙丘的。
塔克拉玛干的沙子非常绵,我们大字形地躺平,大哥指着什么都没有的天空讲,如果是晴天,这里会是什么星,那里会是什么星,银河会是什么样的走向,他所指的地方,仍旧一片虚无。
然后非常意想不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音乐,很多种乐器,驼铃羊铃牛铃,充满沧桑的歌声,多个声部起起伏伏,夹杂着风沙的声音,好像千年以前的商队,人、马、骆驼,在丝绸之路的黄沙中行走。
那一刻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感动,那种感觉太当下了,我眼泪一下就掉下来。其实没有看到满天繁星,是有点遗憾的,但那一刻忽然感觉,能不能看到星星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星星其实就在我们头顶上,不管能不能看到,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
后来大哥点亮了火把,带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走上沙丘,看到演奏者和演唱者们,十几位当地的大叔和爷爷。后来才得知,刚刚的演奏离我们150米远,整个沙漠就是他们演出的声场,他们的嗓音、奏乐,都与沙漠融合地如此完美。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觉的民族音乐,体验感最佳的实景演出。惊喜是,我们进沙漠徒步的时候,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场演出。这些老者都是沙漠边缘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大多数都没怎么离开过塔克拉玛干,他们演奏的乐曲是维族最有名的古典音乐形式十二木卡姆,是非遗。
营地的主理人大哥一个一个介绍他们,介绍他们的乐器,请他们各自solo,有几个还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最年长的一位已经84岁了,他说听说今天有远方的客人,一定要跟着进沙漠演奏。还有一位74岁的老人,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300公里外的县城,只去过一次。他的solo没有起伏,放在我们的音乐审美中,他的技术平平。虽然那把木卡姆已经陪他演奏了五十年,但他其实只会那么两首曲子,一辈子翻来覆去也只是演奏那两首。
营地的大哥告诉我们,那首歌的意思是“当冰川的水融化,当小花帽挂在桃树上,我多么希望你回来,我死去的孩子”,我好像一下就明白了,这首歌为什么唱了五十年,还是这样平平。他的孩子不会回来了,他唱的就是他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南疆的人文,不在历史博物馆,在村落,在人。
我发现有几位演奏者就是我们进沙漠时,帮我们赶骆驼车的大叔,还有几个是帮我们烤羊肉串的大叔,整个营地,其实就只有他们这些人。
后来我们就在篝火边开始像少数民族一样疯狂跳舞了,然后反复跟身边的人拥抱。火焰在沙漠之中异常明亮,就像某种涌动不止的情怀。整晚手机都没有信号,一丝都没有,但是完全没有人感到焦虑,没有人不在享受当下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