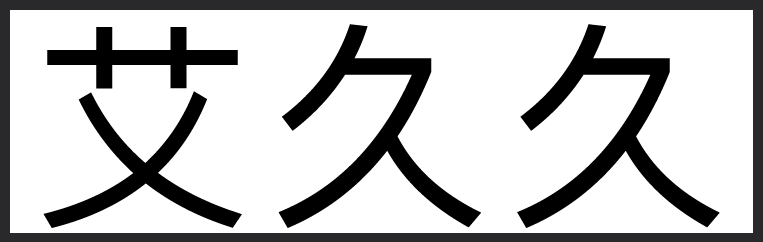《震后一周年,在能登半岛の輪島最...
- Fae·yaa
- 2025-01-25 00:13:04
《震后一周年,在能登半岛の輪島最北端
的志愿日志》
和研究所、福岛医科大的前辈从东京一路向北
前往能登的路上。
车窗外的风景匆匆掠过,
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
几次恍惚间,
以为这是在回新疆的路上,
是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从住处出发去工作地点的路上,经过塌方的山坡,
尚未完全修复的道路和残破的房屋,
无声的叙述着大地震、海啸的痕迹依旧深刻。
而去往最北端、被山、海环绕的一处疗养院工作期间,由于留在这边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感受着人们的破碎、坚韧、无能为力,还有目光里深邃的沉默;
读着白纸黑字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病例、工作日志,
内心时有一种微妙的矛盾:
明明手中的记录如此清晰明了,但我却在它们之间察觉到无形的重量。
那些数字后面,是我无法完全触及的复杂人生,越读越觉自己的渺小与不知所措。
但这种不安,又会被一种理性和冷静所平衡。
或许正是因为无法控制一切,在不可控的范围什么都做不了,我才更应该专注于能做好的每一件小事,用笨拙但诚恳的方式,尽力还原它们背后应有的温度与意义。
而哪怕只是做一些细小琐碎的事,一想到它或许能带来些许实际的帮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并想一直一直、做得更多、更好。
我也在学着把握好一种尺度,
即——“给予支持与接受支持”的关系,是一种包含梯度的关系,它往往会给提供支持的人带来优越感,也会给接受支持的人带来羞辱感。 如果提供支持的人对这种梯度和与之相关的情绪漠不关心,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单方面的行为——在提供支持的人只是满足自己的愿望。
今天天气很好,
日程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早起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最北端的疗养院。
面朝大海办公,
正午阳光灿烂的时候上楼陪伴老人用餐,
再下楼吃自己日日重复的午餐。
去海边散散步,
回来继续办公。
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回到乡下的住处。
条件允许的话,
会和前辈们去周边喝一杯。
这座偏僻岛屿的冬日清冷,
但温暖从不遥远。
的志愿日志》
和研究所、福岛医科大的前辈从东京一路向北
前往能登的路上。
车窗外的风景匆匆掠过,
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
几次恍惚间,
以为这是在回新疆的路上,
是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从住处出发去工作地点的路上,经过塌方的山坡,
尚未完全修复的道路和残破的房屋,
无声的叙述着大地震、海啸的痕迹依旧深刻。
而去往最北端、被山、海环绕的一处疗养院工作期间,由于留在这边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感受着人们的破碎、坚韧、无能为力,还有目光里深邃的沉默;
读着白纸黑字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病例、工作日志,
内心时有一种微妙的矛盾:
明明手中的记录如此清晰明了,但我却在它们之间察觉到无形的重量。
那些数字后面,是我无法完全触及的复杂人生,越读越觉自己的渺小与不知所措。
但这种不安,又会被一种理性和冷静所平衡。
或许正是因为无法控制一切,在不可控的范围什么都做不了,我才更应该专注于能做好的每一件小事,用笨拙但诚恳的方式,尽力还原它们背后应有的温度与意义。
而哪怕只是做一些细小琐碎的事,一想到它或许能带来些许实际的帮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并想一直一直、做得更多、更好。
我也在学着把握好一种尺度,
即——“给予支持与接受支持”的关系,是一种包含梯度的关系,它往往会给提供支持的人带来优越感,也会给接受支持的人带来羞辱感。 如果提供支持的人对这种梯度和与之相关的情绪漠不关心,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单方面的行为——在提供支持的人只是满足自己的愿望。
今天天气很好,
日程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早起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最北端的疗养院。
面朝大海办公,
正午阳光灿烂的时候上楼陪伴老人用餐,
再下楼吃自己日日重复的午餐。
去海边散散步,
回来继续办公。
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回到乡下的住处。
条件允许的话,
会和前辈们去周边喝一杯。
这座偏僻岛屿的冬日清冷,
但温暖从不遥远。